ԭ��(chu��ng) ���Y��ͨ�b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ɹ����P�I
�vʷ���L�ӱ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_ˢ���o��(sh��)�d˥�ɔ���ӡӛ��
˾�R��F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Y��ͨ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̿ƕ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İٿ�ȫ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x���Y��ͨ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䔢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ʡҲ����
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ӡ�C��һ��䲻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Ϥ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څ���ܺ��ď��s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ǛQ���ɔ��s����i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ܳɴ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ڴ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S�����m�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Ԍm���ҵ��Ǘlͨ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
���_�@���ͻ;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S���˵����E���Y�Ͻ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ڳ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

���Y��ͨ�b���_ƪ���ã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κ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θ�ľ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Զθ�ľ���ص����ˡ��ĸߝ���
�ĺ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ľ�≦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Ӿ�����ÿ�^���T���Y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Ɍ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ԥ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㦣������ǃH�ߵ������Ķθ�ľ��
˾�R���ڴ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t�߶��@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Ȅ�Ҳ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ʵ��Д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t���ĵ��¹�h(hu��n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˿̇��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Č����h�ٶθ�ľ�����u��
�ĺ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ײ�ͬ�龳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
ǧ��֮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س���֮���挦����(sh��)ǧ��δ��֮׃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ЌW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á���
�@���Ʊ��صĿ�̖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̶��쮔�r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֪��ȫ���f�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P�����ֱ�Ȼ�|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ļ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¸ĸ�ز����
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l(w��i)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С�׃�֮����
���ڡ���Wƪ����ֱ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ЌW���t���ò��v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λ�鱣ȫ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棨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ı�Ҫ�ֶΣ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
�@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͢�Ие��ɑ]���֞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k�h��F�S�Ƚ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˼���ϵK��
��֮���ijɹ����ܴ�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ʰ����˽y(t��ng)���A�Ӻ�ʿ���Ⱥ�w�ڕr����׃�еĺ����P�С����S�o�y(t��ng)�η�(w��n)���c���y(t��ng)�Ļ����w�ԡ�
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V��֮�g����s��(sh��)��
κ�ĺ��c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�ܺ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Ƅ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ܱ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oҪ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ڏ��s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Ғ�����C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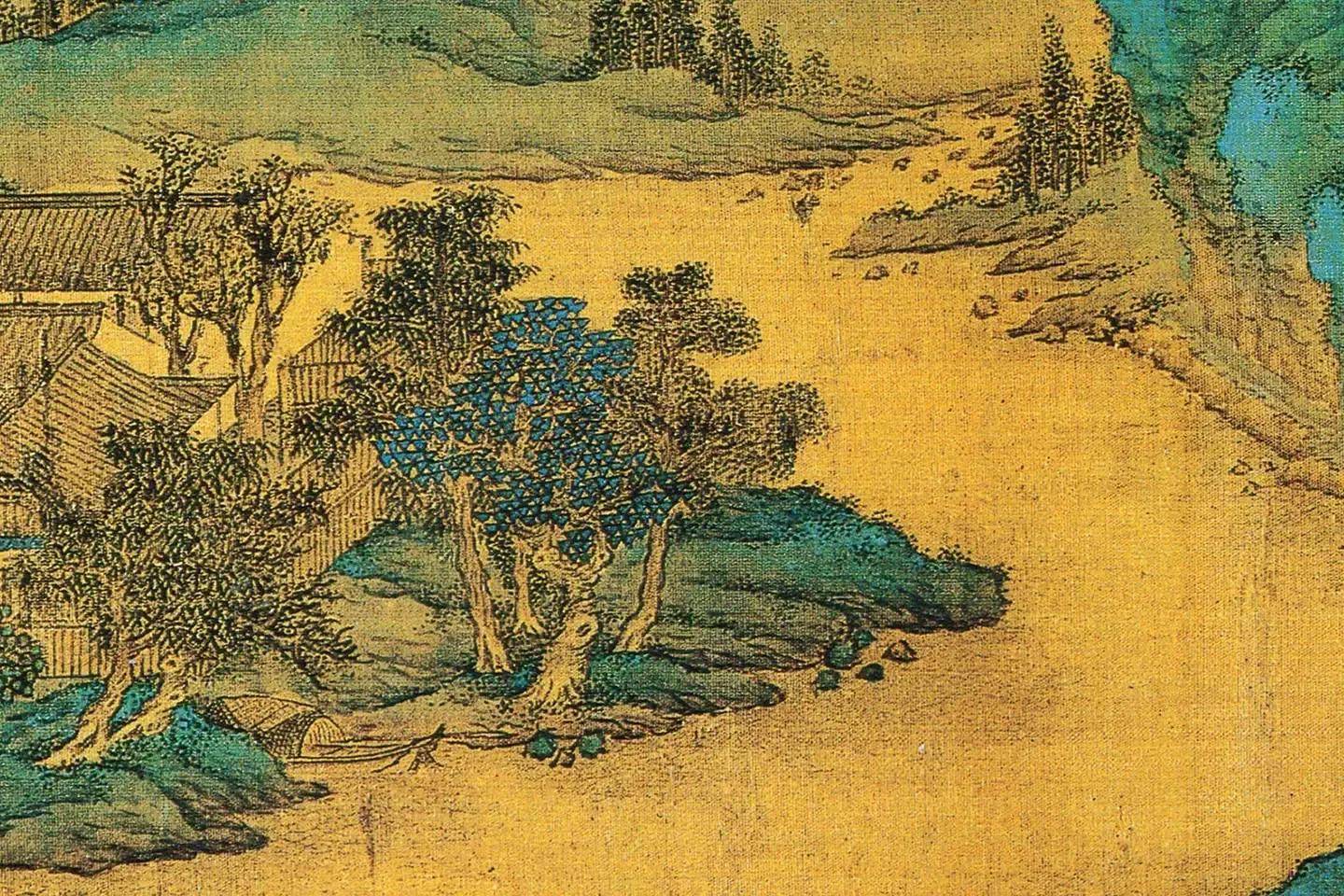
���Y��ͨ�b������ӛ�d���Lƽ֮��(zh��n)�đK��ǰ����
�w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ķ��gӋ�� ���ˡ��ت�η�R�����w��֮���w���錢������̓�ԡ�
����֮�ϣ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G�w����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׃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w��Մ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L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
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ل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ġ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ο�匦��܊�����Ŀ֑���
�Y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錢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K����ʮ�f�w�䱻�Ӛ����w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
˾�R���ڴ�ʹ��ָ�����w��֮ʧ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͂��˵Ľ��]�ɱ����Д���
�vʷ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ơ�
��ʮ���o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挦�����o�Ƶ��տ����A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ߌ��ڑ�(zh��n)���Д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̓��֮�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H�{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ȫ�����A�ěQ�ĺͯ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ل�Փ��һ�����̉m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R�����Ҍ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Ӗ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A�ϵľ�����
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Ԯ����̓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Բ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ƫ�����m��ʿԡѪ�^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Ը����˘O��K�صĴ��r��
�wТ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ڵ�ijЩ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ܴ������г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һ����Ը��
�ɹ������ؾ�һ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܄��_���A���e���c���Ұ�ο�����F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ı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Ϥ����֮̓�������ܰ��լF(xi��n)��֮�挍��

���Y��ͨ�b���h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ۄ�ԃ�ǻ�����[�̿��Q�䷶��
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Q�ڹ⡱��
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e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䱾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ЏU��֮���Ĵ�ɑ���
���x���˘O�µġ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мӣ��� 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rҲ�ԛQ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ܡ���
�ڻ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ú��o��Ҋ���ʾ�Ļ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˽���hՓ�µ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۲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˕r���Р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ѓ�ʯ�����ڡ��ˡ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
ֱ�����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ȥ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ܲ���֮�u¶�����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Σ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ϼ��F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˾�R���u�䡰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ݕr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o���r�C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ڌ�����ԣ�؝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̰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Ї��̽���Әs�ھ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ֵܵĄ�(chu��ng)�I(y��)ʷ��ͬ�ӌ��M�ˡ��M�ˡ����ǻ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ȡ�þ�ɹ���δäĿ�U����
�挦��ʮ���o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ք�ʎ�����罛(j��ng)��Σ�C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I(y��)�D���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Ȅ�����ȡ�ˡ����˞��M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տs���֑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얹̺��Įa(ch��n)�I(y��)���ӏ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M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ϧ�P�]����Ч�治�ѵĹ��S�Ա��挍����
�@�N���Ʊ��صġ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t�Ǟ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L�U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΄��Է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ץס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
�s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v��(j��ng)�L����ܻ��I(y��)�L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֪�M֪�ˡ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淨�t�ܲ��ɷ֡�
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Ұ�r�ġ��M�����K�М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c�s���ֵ����ض��龳�µġ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ɾ����L�h�ġ��M����
���Y��ͨ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Գ�څ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Ȼ����ҊΣ�ڟo����֪�Ε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Εrԓ�w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
�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з�(w��n)���h��

���Y��ͨ�b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R��ӳ�ճ�ǧ�겻׃�����Ե�ɫ��
˾�R��F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ǰ��֮�d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ښvʷ����е��P�I���ӡ�
�oՓ��κ�ĺ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ڌ�̓�����`��֮ʹ���ֻ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ֵ����M���g�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C���@һ�c��
�ɔ��s����ܴ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ڡ�څ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�Ľ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M�y�ˡ��@Щ���Ե����ް�֮����
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x���˚vʷ��߉��Ҳ��ס���ƾ֮��µ�耳���
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Ȳ��ˡ�
��ʷ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Ҋ�ԣ��vʹ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Ԍm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ɹ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Ѻ����鿴����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0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