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坊|早期左翼文學(xué)的多重張力與歷史回響
2025年3月22日,浙江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青年教師學(xué)術(shù)社團(tuán)觀通學(xué)社舉辦“沿波討源:重構(gòu)中國左翼文學(xué)發(fā)生的歷史現(xiàn)場與理論譜系”工作坊,來自中國社會科學(xué)院、南京大學(xué)、復(fù)旦大學(xué)、浙江大學(xué)、中南大學(xué)、華中師范大學(xué)等機(jī)構(gòu)的17名學(xué)者參加了本次活動。本次工作坊持續(xù)一天。與會學(xué)者從理論重釋、史料考掘、跨文化視野等維度出發(fā),圍繞早期左翼文學(xué)的核心議題及張廣海近著《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與階級文學(xué)理論的興起》展開深入而熱烈的學(xué)術(shù)研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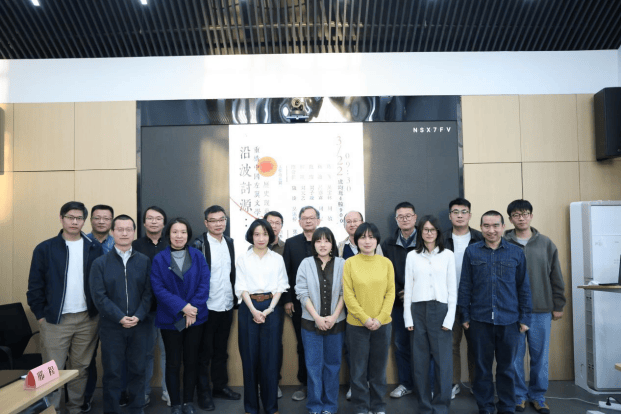
一、“革命文學(xué)”及相關(guān)論爭的再認(rèn)識
重識一般被稱作“革命文學(xué)”的早期左翼文學(xué)及相關(guān)論爭,是本次研討會的核心議題。與會學(xué)者從各自的路徑出發(fā)展開探索,發(fā)表了獨特見解。中國社會科學(xué)院文學(xué)研究所程凱從張廣海近著《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與階級文學(xué)理論的興起》談起,結(jié)合其《革命的張力——“大革命”前后新文學(xué)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》一書寫作經(jīng)驗及近年研究,指出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存在一段漫長的“后史”,有必要將其置于更長的歷史視野中加以考察。他指出,后期創(chuàng)造社在觀念上存在某種模糊性與調(diào)和性,并未實現(xiàn)理論的徹底。他們對由創(chuàng)作、編輯、出版、印刷、發(fā)行、接受等各環(huán)節(jié)所形成的現(xiàn)代資本主義文化生產(chǎn)形態(tài)尚未展開反思,其批判多停留于作品主題和內(nèi)容層面,未能從顛覆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生產(chǎn)機(jī)制的角度或文學(xué)形式革命的角度展開根本性批判。然而,這種未完成的工作卻在解放區(qū)的文藝實踐以及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中得到承接,表現(xiàn)為通過群眾文藝實踐顛覆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生產(chǎn)模式,如取消作者獨立性、淡化出版環(huán)節(jié)等。程凱指出,應(yīng)當(dāng)關(guān)注不同歷史時期之間的聯(lián)系性,將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的漫長“后史”納入考察視野,才能完整把握無產(chǎn)階級文化歷史進(jìn)程的深層邏輯。

山東師范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劉子凌深入闡析了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所蘊(yùn)含的多重張力結(jié)構(gòu),認(rèn)為這些張力結(jié)構(gòu)在根本上呼應(yīng)了知識分子在歷史洪流中的處境問題。他認(rèn)為,其中最核心的張力在于“決定論”與“自由意志”的關(guān)系問題,即歷史發(fā)展究竟是自然進(jìn)程還是主體意志推動的結(jié)果。這一命題不僅關(guān)乎對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的闡釋問題,更觸及“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規(guī)劃未來”這一深層哲學(xué)問題。劉子凌指出,或可以將“革命文學(xué)”及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研究置于歷史哲學(xué)的思考維度,在必然與可能、宿命與意志的辯證關(guān)系中,充分把握其思想內(nèi)涵與時代意義。這一研究視角,也為思考現(xiàn)代知識分子與歷史的關(guān)系提供了重要角度。
南京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葛飛細(xì)致梳理了李初梨、成仿吾、阿英、魯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鄭振鐸等人關(guān)于早期左翼文學(xué)的歷史敘事,探討了早期左翼文學(xué)運(yùn)動中“正統(tǒng)性”“劃時代意義”等問題發(fā)生、演變并被建構(gòu)的歷史過程。他特別關(guān)注左翼陣營內(nèi)部不同派系之間的消長、創(chuàng)作路線的調(diào)整,以及由此引發(fā)的歷史敘事變化,著重分析了這些動態(tài)變化對“文學(xué)革命”到“革命文學(xué)”的形塑作用。葛飛通過細(xì)致的史料分析和闡釋,揭示了左翼文學(xué)話語權(quán)爭奪背后的政治邏輯與文學(xué)觀念博弈,為理解中國“革命文學(xué)”歷史敘事的變遷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。

復(fù)旦大學(xué)中文系劉天藝基于近年研究旨趣與經(jīng)驗,重點談?wù)摿嗽凇按蟾锩睍r期的革命文學(xué)史料發(fā)掘、整理與闡釋過程中遇到的關(guān)鍵問題,并嘗試建構(gòu)了研究方法論。他特別對“革命文學(xué)”概念的指稱問題進(jìn)行了批判性反思,指出該術(shù)語在學(xué)科研究中呈現(xiàn)出內(nèi)涵與外延的模糊性,進(jìn)而導(dǎo)致了其與“左翼文學(xué)”等相鄰概念的混用。他強(qiáng)調(diào)在具體的歷史研究中必須審慎處理這一術(shù)語,既尊重歷史文本的原生語境,又要建立清晰的概念邊界,以此來避免因概念不清造成的研究偏差。
二、早期左翼文學(xué)個案研究
與會學(xué)者還深入到早期左翼文學(xué)的個案當(dāng)中,展現(xiàn)出早期左翼文學(xué)的豐富性,在域外論爭、作家心態(tài)、形式批評、感官敘事、美學(xué)淵源等方面,提供新的研究視角。中南大學(xué)人文學(xué)院吳寶林談?wù)摿巳毡緦W(xué)界對中國左翼文藝研究史料的整理,以及自己的資料探索和發(fā)現(xiàn),進(jìn)而對早期“左聯(lián)”在東京兩個分支組織“新興文化研究會”與“中國社會科學(xué)研究會日本分會”的形成狀況及其展開的“理論戰(zhàn)”進(jìn)行了深入發(fā)掘,揭示出這場“理論戰(zhàn)”在批判模式、政黨介入等方面與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存在歷史相似性。他指出,某種意義上這是20年代末論爭的域外延續(xù),印證了程凱剛才提出的“‘革命文學(xué)’論爭存在一段漫長后史”的觀點。因此,若以更大的歷史視野將其統(tǒng)攝起來,這一域外論爭亦可被視作四十年代及“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”諸多“理論戰(zhàn)”的“先聲”。吳寶林還講述了他在研究過程中深切體會到的歷史的“驚心動魄”,即論爭表面上是意氣用事,或只是理論分歧,但實際上對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產(chǎn)生了劇烈波動,并造成了一定的歷史后果。這一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胡風(fēng)的革命文藝思想,還拓展了“左聯(lián)”研究的國際視野,為理解中國左翼文學(xué)運(yùn)動提供了必要的視角。

杭州師范大學(xué)人文學(xué)院呂彥霖通過1983年姚雪垠書信等史料,還原了1938年“《風(fēng)雨》事件”的真相與細(xì)節(jié),指出這一事件被姚雪垠在1986年、1987年修改《春暖花開的時候》時不加涂抹地加以呈現(xiàn),造成小說“既左又右”的曖昧面貌。呂彥霖認(rèn)為,在姚雪垠身上存在著鮮明的“革命文化人”秉性,即“革命”與“文化”之間存在著某種動態(tài)的平衡,當(dāng)其中一方受到壓制,平衡被打破時,另一方則會強(qiáng)烈反彈。而“《風(fēng)雨》事件”作為有價值的案例,展現(xiàn)了“革命文化人”在政治洪流中的搖擺姿態(tài)。
浙江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邢程認(rèn)為瞿秋白的“擬魯寫作”體現(xiàn)出鮮明的“形式無意識”,即瞿秋白雖然在其魯迅論中主要從內(nèi)容主題的戰(zhàn)斗性質(zhì)和意識形態(tài)立場的維度來建構(gòu)魯迅,但其1933年以“魯迅風(fēng)”寫就的12篇雜文,首先摹仿的實際上是形式與風(fēng)格。她還借用本雅明對貢多爾夫的批評——如同“猴子一樣在樹枝間跳來晃去,只是為了不必接觸地面(即文本)”,對以《〈魯迅雜感選集〉序言》為代表的論說模式的方法論作出反思,認(rèn)為未能深入文本的內(nèi)在形式結(jié)構(gòu),揭示其形式自律性。對于歷史研究中的“同情的理解”立場,她在肯定其意義的基礎(chǔ)之上,還認(rèn)為當(dāng)下學(xué)者不應(yīng)慣性地沿襲前人的材料與方法,混淆“材料文獻(xiàn)”與“經(jīng)典文本”的本質(zhì)區(qū)別,進(jìn)而導(dǎo)致真正有效的批評方法被遮蔽。
復(fù)旦大學(xué)中文系康凌以殷夫的革命實踐及《在死神未到之前》《孩兒塔》等詩作為討論中心,指出殷夫大革命時期的詩歌創(chuàng)作呈現(xiàn)出鮮明的感官化特征,即善于通過聽覺、嗅覺、視覺等感覺經(jīng)驗來呈現(xiàn)革命者的身體體驗,這種獨特的感官書寫,使革命受難者的身體在文本中超越了單純的描寫對象,轉(zhuǎn)而成為連接詩歌藝術(shù)表達(dá)與社會革命實踐的重要媒介。他還結(jié)合魯迅閱讀殷夫詩歌時的不安感受,揭示出殷夫與魯迅等左翼作家共享著理解“亡友”及“鬼的世界”的感官機(jī)制與心理方式。該研究不僅探討了殷夫詩歌創(chuàng)作的形式特征,更深入揭示了感官敘事在左翼文學(xué)內(nèi)部的某種普遍性。

南京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顏煉軍同樣關(guān)注殷夫詩歌,但側(cè)重分析殷夫詩歌的精神與文學(xué)資源,他通過對《花瓶》《呵,我愛的》《孩兒塔》等一批文本和相關(guān)意象群的細(xì)致解讀,指出殷夫在精神資源與寫作主題上與聞一多、朱湘、何其芳等詩人有相通之處,像二十年代許多詩人一樣,他也曾以拜倫、雪萊、濟(jì)慈等西方浪漫主義詩人為師。像“死神”“流浪人”等意象,皆能在十九世紀(jì)浪漫主義詩歌中找到源頭。他由此揭示了左翼詩歌與浪漫主義傳統(tǒng)的復(fù)雜關(guān)聯(lián),為理解左翼詩歌的美學(xué)質(zhì)地與復(fù)雜構(gòu)成打開了空間。顏煉軍還特別關(guān)注到殷夫晚期詩歌中出現(xiàn)的“海燕”這一高爾基式意象。他指出,這種新意象的引入可能反映了兩種創(chuàng)作狀態(tài):或是詩人思想發(fā)生實質(zhì)性轉(zhuǎn)折,或是現(xiàn)代作家常見的“寫作分身術(shù)”。雖然殷夫整體上呈現(xiàn)出激情與行動的高度一致,較少顯露“分裂”,但透過這些文本細(xì)節(jié),依然能看到殷夫詩歌中的曲折情感和內(nèi)在裂隙。
浙江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周旻以巴金早年的“上海時期”為脈絡(luò),通過細(xì)致的史料梳理,勾勒出了1920年代早期上海無政府主義共同體的大致輪廓,分析了共同體內(nèi)部思想觀念的“和”與“不同”,并以自由書店及《自由月刊》等文化陣地為中心,探討了巴金等青年知識分子如何通過出版、翻譯等文藝實踐表現(xiàn)自我的無產(chǎn)階級文學(xué)觀念等問題。周旻還對無政府主義思潮與“革命文學(xué)”思潮的分歧進(jìn)行了深入剖析,指出沖突集中體現(xiàn)在對革命本質(zhì)的理解差異上,前者主張漸進(jìn)式的社會進(jìn)化論革命,強(qiáng)調(diào)個人自由;而后者則堅持激進(jìn)的階級革命論,推崇政治斗爭,這種根本性的理念分歧使兩派在1920年代末期的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中產(chǎn)生了“不可調(diào)和的對抗”。該研究拓寬了中國左翼文學(xué)的起源路徑,有助于我們在現(xiàn)代中國激進(jìn)思潮的多元譜系中更好地認(rèn)識中國左翼文學(xué)的發(fā)生。
三、左翼文學(xué)研究的方法論反思
由“革命文學(xué)”相關(guān)問題出發(fā),諸位學(xué)者還圍繞“如何認(rèn)識左翼文學(xué)、左翼理論”等問題,反思了當(dāng)前左翼文學(xué)研究的方法論。山東師范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劉子凌提出了具有啟發(fā)性的觀點:左翼文藝?yán)碚摫举|(zhì)上不是一套認(rèn)識論體系,而是一種具有鮮明價值取向的倫理觀。他認(rèn)為馬克思主義對當(dāng)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巨大吸引力,主要不在于其解釋世界的理論力量,而在于它承諾了一種個體救贖的可能性,為解決人生困惑提供了新的倫理指南。因此,他認(rèn)為對左翼理論在成為共識性話語之前的傳播過程的深入探索,能夠揭示人們?nèi)绾谓柚@一思想體系來理解個體、文學(xué)與世界之間的張力關(guān)系。劉子凌對歷史洪流中的個體存在及倫理抉擇的關(guān)注,深化了我們對中國早期左翼文學(xué)中的知識分子主體問題的思考,為研究左翼思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視角。劉子凌同時提出,理想的左翼文學(xué)研究應(yīng)能夠很好地激活歷史瞬間,既通過史料還原歷史現(xiàn)場,又能避免陷入史料泥潭而不能自拔;研究者既需要運(yùn)用“后見之明”的理性分析,又要保持對歷史當(dāng)事人所處語境的“同情之理解”,方能更為深入地接近歷史對象。
中南大學(xué)人文學(xué)院吳寶林對當(dāng)前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研究的范式轉(zhuǎn)型進(jìn)行了反思,指出近年來諸多“各領(lǐng)風(fēng)騷三五年”的“轉(zhuǎn)向話語”雖然拓展了研究邊界,如打破了革命敘事的單一性,但也帶來了“扁平化”歷史動力的研究困境。他特別強(qiáng)調(diào)了張廣海著作中所提到的“人情物理”這一概念在左翼文學(xué)及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研究中的意義,認(rèn)為理想的研究應(yīng)當(dāng)保持對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內(nèi)在脈絡(luò)和“現(xiàn)代中國”生成機(jī)制的把握。
華中師范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吳述橋關(guān)注的是左翼文藝?yán)碚撝小敖M織”話語問題。他首先考察了“組織”話語的跨語境傳播,從語義上梳理了“組織”的詞源和演變過程,指出中國的“組織”話語傳播經(jīng)歷了一個由日本傳至俄國再傳至中國的曲折過程。他以茅盾創(chuàng)作為例,指出左翼文學(xué)的發(fā)展始終貫穿著“組織”的思想觀念。這種組織性體現(xiàn)在兩個層面:在創(chuàng)作指導(dǎo)層面,黨組織通過意識形態(tài)引導(dǎo)直接影響作品的主題思想,文學(xué)批評家則扮演著具體指導(dǎo)創(chuàng)作的角色;在文學(xué)生產(chǎn)機(jī)制層面,“左聯(lián)”及中共地下讀書會等組織形式承擔(dān)著意識形態(tài)生產(chǎn)的功能。他指出,左翼文學(xué)在組織文學(xué)生產(chǎn)方面形成了獨特模式,因而有必要重視“組織”作為方法論概念的理論價值與歷史意義,深入探索組織化運(yùn)作與左翼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之間的復(fù)雜互動關(guān)系。
浙大城市學(xué)院人文學(xué)院范雪分享了關(guān)于“中國知識分子階級定位問題”的思考。她以郁達(dá)夫后期小說《出奔》為例,認(rèn)為郁達(dá)夫在他關(guān)于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判斷的表述中使用的“荒謬”一詞可能相當(dāng)關(guān)鍵。荒謬,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判斷階級的方式。這可能與當(dāng)時中國并沒有發(fā)生英、美所發(fā)生的機(jī)器蕩平世界、物質(zhì)大生產(chǎn)的事實有關(guān)。在這個事實世界的感覺里,那個要被警惕和反對的,不是“物”的掌控者,而是傳統(tǒng)上長期與統(tǒng)治關(guān)聯(lián)在一起的“文”。邢程對范雪的觀點表示贊同。她以《魯濱遜漂流記》為例,指出作品在時態(tài)運(yùn)用上的矛盾折射了資產(chǎn)階級上升時期理性精神與冒險沖動之間的心靈張力。借此視角,我們或能更好地觀察早期左翼文學(xué)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結(jié)構(gòu)與內(nèi)在矛盾。
浙江理工大學(xué)史量才新聞與傳播學(xué)院曾小蘭分享了她對張資平的研究心得,認(rèn)為張資平的形象長期被扭曲與遮蔽,實際上張資平展現(xiàn)出與創(chuàng)造社、太陽社成員不同的理性思考特質(zhì),而對此一領(lǐng)域的探索,不僅能促進(jìn)研究者自身的學(xué)術(shù)成長,更有助于還原一段歷史真相。

四、《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與階級文學(xué)理論的興起》研討
在浙江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陳奇佳主持下,與會者還圍繞浙江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張廣海的近著《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與階級文學(xué)理論的興起》(北京大學(xué)出版社2024年版)展開了圓桌討論。
張廣海首先講述了該書寫作緣起與立場,表明該書力圖“既站在左翼與右翼之間,也站在左翼與左翼之間”,在破除左翼文學(xué)研究中常見的“魯迅中心主義”預(yù)設(shè)的前提下,探索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的真相與意蘊(yùn)。他從“事”與“理”兩個角度談?wù)摿嗽摃既ぃ胤窒聿⑻接懥恕昂笃趧?chuàng)造社、太陽社是否蓄意發(fā)動魯迅批判”“彭康的入黨時間考辨”“茅盾的廬山行跡考辨”“后期創(chuàng)造社的理論批判潛能為何被抑制”“階級性與人性之辨該如何認(rèn)識”“后期創(chuàng)造社的再定位與太陽社文壇活動的再認(rèn)識”等既具有一定趣味、也值得繼續(xù)進(jìn)行理論探索的問題。其次,北京大學(xué)出版社高迪基于該書的編輯經(jīng)驗,發(fā)表了對學(xué)術(shù)“生產(chǎn)”與“寫作”的見解。她認(rèn)為,編輯作為學(xué)術(shù)生產(chǎn)鏈條中的特殊角色,能夠目睹稿件最原始的狀態(tài),因而尤其能關(guān)注到作者寫作的緊迫感與思考的張力,并強(qiáng)調(diào)在“生產(chǎn)”的功利性與系統(tǒng)性之外,學(xué)術(shù)著作應(yīng)保持創(chuàng)造性、切身性和敞開性。
接著,與會學(xué)者圍繞該著進(jìn)行了多維度的深入討論。陳奇佳指出,他從張廣海著作中特別關(guān)注到了夏曦、何畏、沈澤民、張聞天等人物,這些個案折射出許多左翼文學(xué)史上值得深入探討的歷史問題。程凱指出,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史的敘事呈現(xiàn)出以“理論論爭”為核心的特征,體現(xiàn)為“文化政治斗爭史”的敘述傾向。他以“漩渦”為喻,形象描述了這種高度壓縮的理論話語所產(chǎn)生的強(qiáng)大影響力,而正是這種復(fù)雜的理論互動構(gòu)成了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發(fā)展的內(nèi)在動力。他進(jìn)而指出了“實證主義”方法的局限性,認(rèn)為過度強(qiáng)調(diào)實證可能導(dǎo)致文學(xué)史研究中“革命內(nèi)在動力”的消解,因此,如何深入探討文學(xué)論爭史仍是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研究中有待深入展開的核心問題。對于文學(xué)論爭研究,程凱認(rèn)為,需要注意到其“表層”與“深層”的雙重結(jié)構(gòu),研究者需要穿透論爭的外表,把握隱藏于其下的邏輯脈絡(luò)和實質(zhì)。程凱認(rèn)為,“魯迅中心主義”這一現(xiàn)象根植于中國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文化的選擇,即瞿秋白等革命理論家試圖尋找區(qū)別于后期創(chuàng)造社“觀念突變”的模式。這一選擇過程同樣延伸至80年代的后續(xù)歷史之中。
杭州師范大學(xué)文化創(chuàng)意與傳媒學(xué)院周敏以偵探小說為比喻,指出張廣海該著通過偵探式的嚴(yán)謹(jǐn)史料考據(jù),還原了被當(dāng)事人有意或無意遮蔽的歷史真相,同時又能在證據(jù)難以觸及的領(lǐng)域,憑借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力,從盤根錯節(jié)的文字陳述中精準(zhǔn)把握歷史人物的心靈軌跡。他認(rèn)為張廣海的研究不僅體現(xiàn)出“笨功夫”與“真智慧”的較好統(tǒng)一,而且在理論批評與史料考證的結(jié)合方面,具有了“以厚重約束輕靈,以輕靈舉重若輕”的學(xué)術(shù)品格,這使得該書一方面“雅俗共賞”,具有極強(qiáng)的可讀性,另一方面又不失專業(yè)研究的深度,能扎實地推進(jìn)相關(guān)領(lǐng)域的研究。
吳述橋指出,張廣海的近著對于碎片化的歷史研究具有很好的方法論意義:在實證層面,通過扎實的史料爬梳提供了確切的歷史細(xì)節(jié);在理論層面,又對重要問題進(jìn)行了深入探討。這種將微觀考證與宏觀思考相結(jié)合的研究路徑,既避免了空泛的理論推斷,又超越了瑣碎的史料堆砌,在“史”與“理”之間保持了富有張力的平衡。
顏煉軍先論及張廣海此前出版的《左聯(lián)籌建與組織系統(tǒng)考論》一書,認(rèn)為其對史料的考辨和梳理特別精彩,寫作上有卓異的個人風(fēng)格;繼而評價新著在史實考證與理論辨析的結(jié)合上,更上層樓,做了非常出色的推進(jìn)。同時他也懇盼其后續(xù)研究或可在此基礎(chǔ)上,在文學(xué)作品的維度打開更廣闊的空間,做到兼顧“史”“理”“文”的立體和呼應(yīng)。
康凌指出學(xué)界長期存在著“一體化”的左翼知識的固化框架,左翼內(nèi)在的動力與勢能被封存于這一框架之中,而張廣海的研究則將左翼被壓抑的內(nèi)在動力重新釋放,通過對左翼理論野蠻生長時期的“非主流作品”的發(fā)掘,呈現(xiàn)了被主流敘述遮蔽的理論洞見與實踐挫折,較好地復(fù)現(xiàn)了歷史現(xiàn)場的多元樣態(tài)。
對于張廣海著作中對“階級性與人性”議題的關(guān)注,葛飛建議可嘗試突破文學(xué)研究框架,建立縱向的研究視野,將視域從創(chuàng)造社刊物擴(kuò)展至五四以來的中共刊物,系統(tǒng)考察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傳播歷程與接受機(jī)制,加強(qiáng)理論闡釋。程凱則建議,進(jìn)一步超越依據(jù)馬克思《1844年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哲學(xué)手稿》討論階級性與人性論爭的視角。
吳寶林認(rèn)為當(dāng)前文學(xué)研究存在認(rèn)識論和方法論的雙重困境:一方面研究者往往難以擺脫當(dāng)代視角,容易將“當(dāng)代性”投射到歷史現(xiàn)場,造成對歷史的扭曲解讀。另一方面,“還原主義”式的研究視角又會局限于“歷史風(fēng)貌”的刻畫,而難以深描出“躍動的歷史”。他指出理想的研究狀態(tài)應(yīng)保持“游移”的特質(zhì)——研究主體與歷史對象之間形成一種動態(tài)的、游移的關(guān)系,進(jìn)而肯定了《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與階級文學(xué)理論的興起》一書游動于不同歷史對象之間的立場與姿態(tài)。劉天藝則指出,張廣海該著努力擺脫既定左翼文學(xué)史的敘述框架,將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論爭還原到1920年代中國革命尚未定型的生成階段之中,辨析了“革命文學(xué)”與種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復(fù)雜交纏關(guān)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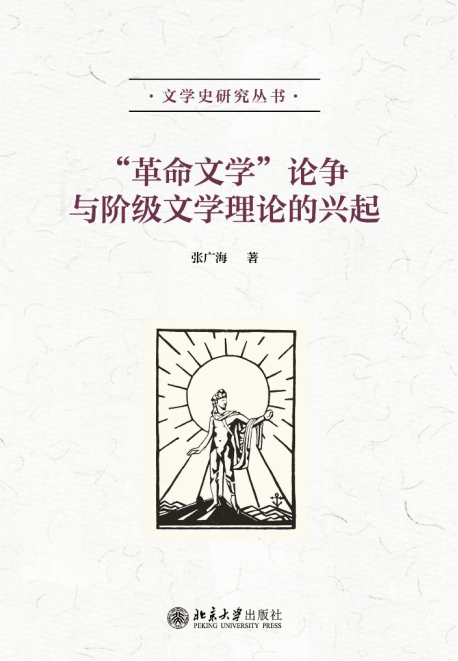
本次工作坊重新審視了左翼文學(xué)的發(fā)生機(jī)制與譜系演變,既聚焦文本細(xì)讀與歷史現(xiàn)場還原,亦關(guān)注“革命文學(xué)”的歷史回響,呈現(xiàn)出方法論上的開放性與問題意識的前沿性。工作坊既深化了對早期左翼文學(xué)復(fù)雜性的理解,也為后續(xù)研究的開拓提供了可能的學(xué)術(shù)生長點。








發(fā)表評論 評論 (1 個評論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