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���Ļ��W(xu��)�ߏ���Մ���~����Խ�r���Ԋ�⌦Ԓ
�f���Ї��ŵ��ČW(xu��)�Ďp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_����ƪ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w�����ڱ��εľ����跻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߅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м�ʎ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W(xu��)�ߏ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Ļ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ǿ����δ��L(f��ng)�ǵġ�����ܴa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ӹŽ�ġ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~��ÿһ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δɢ�Ĝ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x�g���c���˵ı��g�p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`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(li��n)�Ž���еľ���~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Ѿ��ɵ�耳����ܴ��_һ��ͨ��ǧ��֮ǰ�ĕr��֮�T���҂��QҊ�Ǖr��ɽ�ӡ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퍵��о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Ѫ�}�c�ض�
Մ�����~�ĜY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Ҫ�x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Ǒ{�����L��Ԋ�����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衯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p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ĞE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ԭ�Ř���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`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ѭ���@Щ�ƓP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Ў����ǡ��һ����ˮ��|�����Ľ^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ġ��G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Џص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擴������c�_韵��⾳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ʢ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I���P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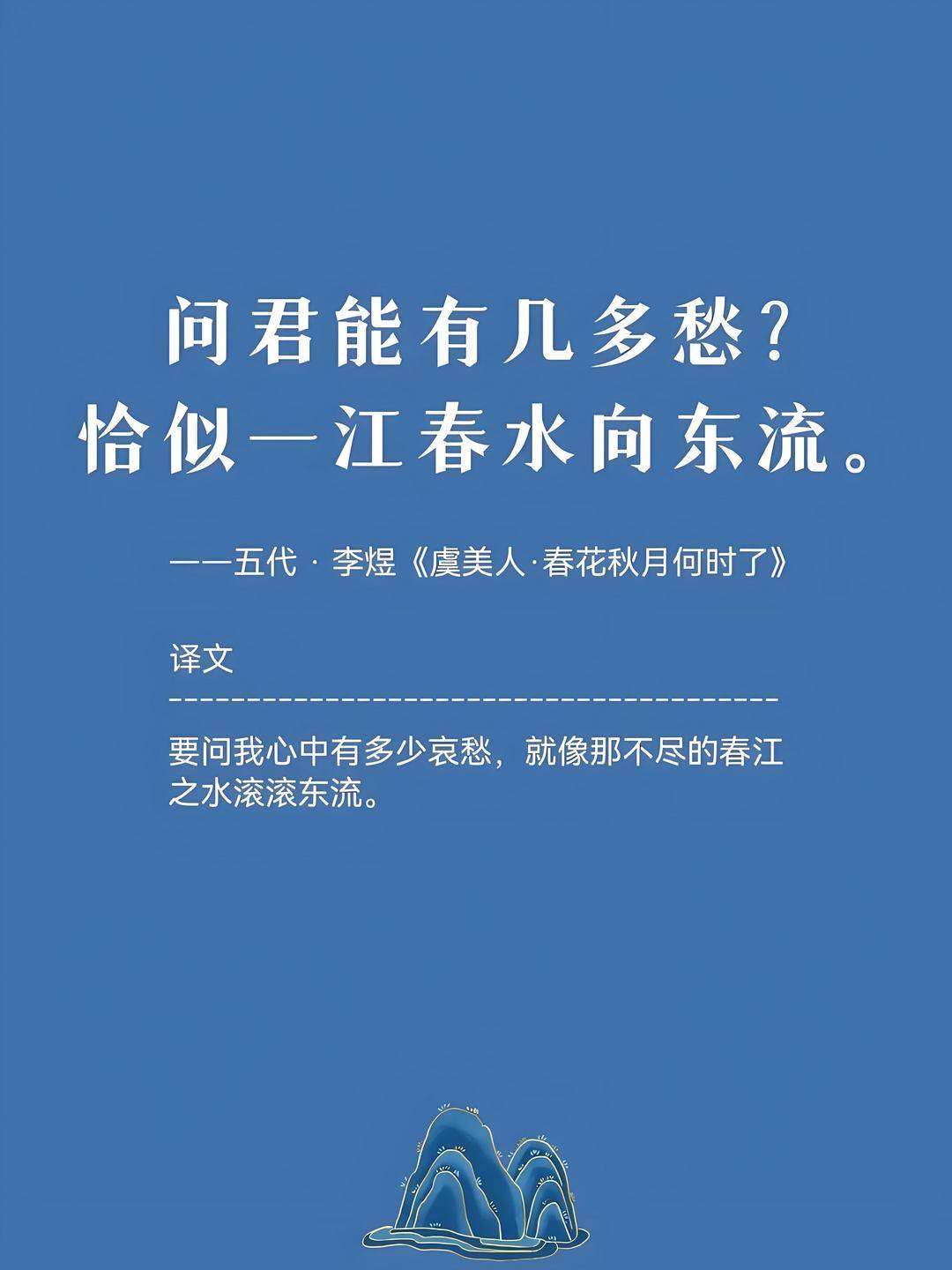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�⏊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x���_�c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Ƚ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Ԋ�Ԏ��ġ�ʿ���⡱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𡱡������ǾƘ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d֮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^�ɿ�߅�̈́e��㰐�֮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˂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ɡ��о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¡����M�x�˵ĜI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ɻ����L���X���ķ��Aʢ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о�ˮ̎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~�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ˌ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ӵؚ⡯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^���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܂������ܼ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ġ����՟���D��
�ڏ����Ľ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~��ǡ��һ����Ⱦ�_�ġ����՟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ÿһ�䶼���؝��c�`�����@һ�r�ڵ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顱��P�����ĵļ�ā���|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п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桱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~�L(f��ng)���ԡ��o���κλ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e�ӵ����š���ͥǰ�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w����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g�M��ʿ���ď����cͨ���x����Ʒһ�K�ز裬��ζ�d�L��
�����̎��t���ˎ֡��V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˷Q�䡰С�̡����c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(d��ng)�r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ղ��ƚw�����Ќ��f�˵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˅s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ѿ̹ǵĠ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V�Ļؑ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Ѫ���x���˱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^���nj���s�~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p�Ɖ����o߅�z�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P�|�����ij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ӯ���o߅�z���Ƴ�w��d�L���B���ϵğ��궼Ⱦ�������ϵĠ��죬�y���K�Y��ʹ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f�˺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Ĩ�������B˥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ٛ����ɽĨ�ƌW(xu��)ʿ������̖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˺��P(gu��n)�L(f��ng)�c�¡����Ի��_֮�Z���M�V��ı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L(f��ng)�½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ŪӰ�����Hһ��㹴�ճ���ҹ�»�Ӱ�uҷ���`��֮�����{�˫@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ĵ�ɫ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еġ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~�ǡ����՜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L�衯�������ˎּ҇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ǵ��P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׃��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ĹP�˶��ˡ���־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ɵ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s�ɵľ�������?c��)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?/div>



1. 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Ѫ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҇���(d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
�K�Y�m�鱱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|ȥ�����ԱM��ǧ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ġ���Ů���L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һ�e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ѡ����¾��硪����ڹő�(zh��n)���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d���Ŀ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_��Ҳ�~�Ĵ����˽��Ӻ�����ĉ�韚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~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λ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~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Mǻ�ļ҇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Mÿһ���־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B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j���ɳ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ѕr�Տ�(f��)ʧ�صĉ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־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ɽ�ڲ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ȥ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ǣ�����һ�䡰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M��Ӣ��ĺ��ı����c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u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ǡ��~���Є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䶼�������ӵij��\���x���˟�Ѫ���v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ˁy���в����Ĉ�ؑ�����w�ġ��M���t��ŭ�l(f��)�_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m�c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·�ƺ��¡����M��־��һ�䡰Ī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ձ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ĵĊ^�M̖�ǡ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ß�Ѫ���͵ľ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2. ��s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رM��ɣ�c����
���ε���s�~���m���˱��εĜ؝����s���ˎ־����c��ɣ�����־�䶼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ӡӛ��
�����ǡ��~���p�^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䡶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ʮ�Ę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ʎ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⾳���M�P�ݳǵđ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շ��A�Ķ�ʮ�Ę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ɘ��²���ʎ������ֻ�б�����¹��c�o�ı������~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Ӣ���u�顰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ā�ĉ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ϳɳ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һ��㌢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ʒɪ�����ϡ��x�ˡ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˓]֮��ȥ�ij�w���䡶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ƪ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˼�w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ĵ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˼���c�r��ľd�L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顰ǧ�ŵ�һ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ǙM����ε��~�����E��ǰ�ڡ���ӛϪͤ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w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M����Ů�ċ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Ғ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K���ݡ����t�LJ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̹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ǂ������\�c�r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ġ�Ů��ʷԊ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��Ѫ�I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퍣�ǧ��δɢ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Ļ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~�IJ��Ƿ���ڲ����^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Ѫ�}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ľ�����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칝(ji��)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f���Ԫ��ص�Ԋ�⣬��ο�҂��Ľ��]�cƣ�v��
�����⾳�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䣺�ܽ܂�����ɡ��С�����ɫ�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еĺ�����s��ë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�ա��һ�؝��ϲ��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ĺ��~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B�ճ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ҵ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ƣ�v�r���xһ���K�Y�ġ�����âЬ�p���R���l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_��˼��r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^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L�r�����M�ڳ���ĺĺ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˜���Ěw������ã�r��Ʒһ����εġ�ɽ��ˮ��(f��)�ɟo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ʰǰ�е�����

�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IJ�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ÿһ����ͨ�˵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oՓ�ǹ��˵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߀�ǽ��˵Ľ��]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־����ҵ�ο�����ֻҪ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𡮵�Ը���L����ǧ�ﹲ�Ⱦꡯ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r���𡮚wȥ��Ҳ�o�L(f��ng)��Ҳ�o�硯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Ǐ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r�⾫��ᄾ͵ļ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ֵĸ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ǚq�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Խ�Ž�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^�B���δ���ɽ�ӟ�����һ�^�B�����˵�ϲ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^�q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¹�𨝍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˲�g���p�pߵ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Ԋ���c���顣

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ؼs�uՓ�T���Y���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Ѹˇ�g(sh��)�W(xu��)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ɝh�����Ļ��ƏV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ƏV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w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2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