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(xi��)��|�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|���ĵ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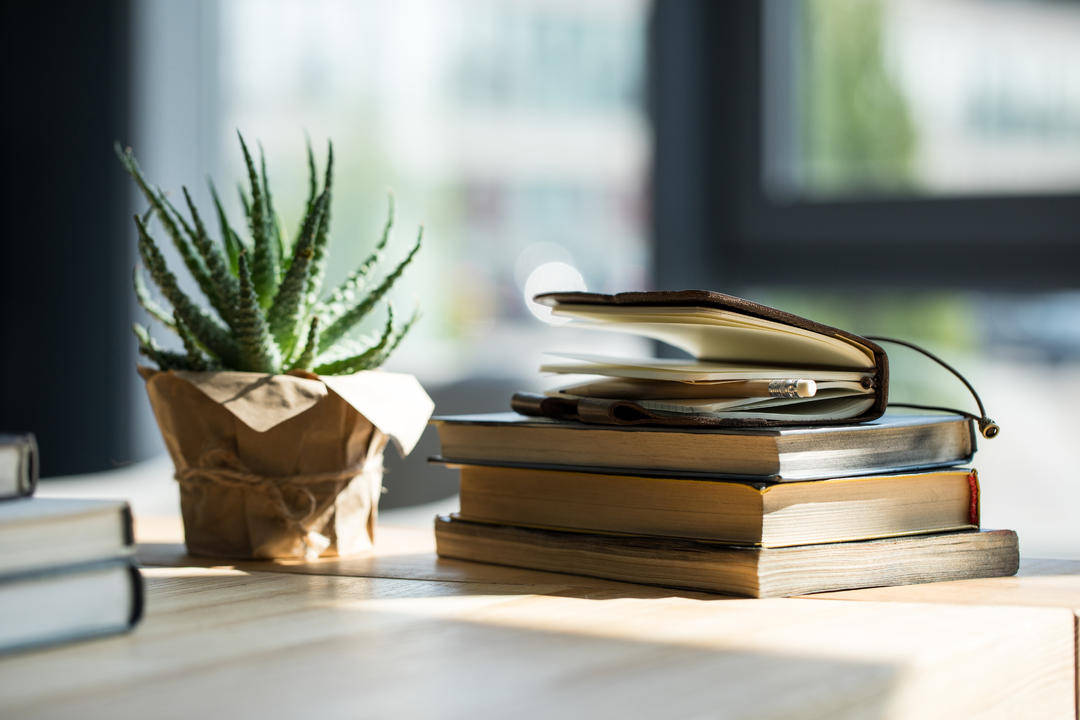
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ɩ���ڻҶ������ͳ�ʮ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hՓ֮�����㶨�f(shu��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ҵ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һ�R��ؼ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Ѹ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ô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o(w��)��Փ��
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ߗ��ɩ���ɺܴ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^(gu��)ĸ�H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@�Σ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Ԟ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⚢���wҲ�Ƶ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Ҳδ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ĸ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N�³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^(gu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(ch��ng)��
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һ�ٶ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@����Ʒ��Ҳ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Ȼ��һ�N�п�����Ѹ��ɶ�](m��i)�o�Լ��ĺ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߀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
�ĸ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Ѹ�Dz�ϲ�g���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̱�����(xi��)�ú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AҎ(gu��)��һ�ӵ��˄�(sh��)��̎̎���˅����vԒ��ʽ��Ѹ��һ�ɷ��С�����̝���b���@ô�ߵ͵�С�_�����ܵ��@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(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x�ߺ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Ǘ��ɩ�ڽo�ό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?du��)�Ҷѵġ��ɲ족�@�ÿ��⣬�·���֪����߅�Ж|����ȥ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ݻ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\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Ұl(f��)�й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⚢��
���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Ը��ό�(sh��)�[�̣��Ҍ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r(sh��)���x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͵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ˎ��|�����ɗl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Ă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t�͠T�_(t��i)��һ�U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еIJݻң��҂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ǟ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ǻң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صķ���)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̵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(l��i)�d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r(sh��)һ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顰ĸ�H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Dz��ذ��ߵĖ|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(t��ng)���Լ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ό�(sh��)�ͽ����c��߀���x��ȥ͵�����ټ��M(j��n)�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ֺη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o���˰�ʾ���c���](m��i)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Ą�(d��ng)�C(j��)��
ԭ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c����׃�ó�Ĭľ�G���@�N�D(zhu��n)׃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�̵ġ����y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ČW(xu��)ʷ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ձ��h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Ѹ�ČW(xu��)�С��^���cϣ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Y(ji��)β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·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ҡ��Ą�(l��)ֶ�Ӻꃺ�c�c���ă���ˮ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ϵij��壺���Ҿ��c�c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@�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ĺ�݅߀��һ�⡭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ݻ����@�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˟o(w��)��Փ����ʽ�Ҵ��˽Y(ji��)��Ҳ�S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ė��ɩ���Dz���Ҳ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o(w��)�˲¼ɶ���(d��o)�¡���ԩ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Ͻ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ˣ�Ҳ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Λr���ɩ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֮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ε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ǡǡչ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(hu��)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ĵ�֣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Ե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֮�g��ԓ�еĸ�Ĥ��
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Ѓ~�ߵ���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ı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](m��i)�н�¶�i�ף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չ�F(xi��n)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(g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෴�������ĽҕԴ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w��ij����Ҳ̫������ʼ�K�����ٸ�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һ�N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l(shu��)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ֻؓ(f��)؟(z��)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Լ��x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
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ʲô�ǹ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Մ���@���O(sh��)Ӌ(j��)����ҷdz��ڴ����ܽo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_�д𰸡��](m��i)�뵽���w��o���Ĵ����s�ǡ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l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ģ��ǡ��AҎ(gu��)���ɵ���߀���c���ɵģ��ǾͲ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ƪ����ˈA�M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ǻ�ζ�o(w��)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Ĭ�ǽ���
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Ѹ�ĹP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ڡ�͵���Ķ��Ӳ��١��硶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(sh��)�˵ġ��`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ӂ�͵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h�����@Щ�О���龳��һ�ӣ��Y(ji��)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ݻ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�s��һ�N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Ƿǵđ�����^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֮��ζ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S�؏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ͬ�˵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(ju��)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ڰl(f��)����һֱ�߂������Ĝض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ݻ�֮��ֻ�С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ס���ǡ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Ѻ����鿴����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(p��ng)Փ �u(p��ng)Փ (2 ��(g��)�u(p��ng)Փ)